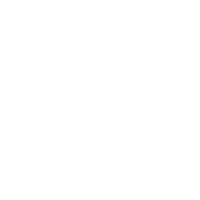11月18日,由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为村发展实验室、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北京为村互联网科技研究中心发起,腾讯学堂、腾讯文化、腾讯北京总部党委协办的“为村讲坛”第三季第4期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合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曹斌作题为“日本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措施和借鉴”的报告。
以下为内容精华版:


• 中高收入阶段的农业政策转型
日本在经历二战后的经济恢复期后,逐渐步入中高收入阶段。在这一阶段,农业政策面临着从数量政策向收入政策的转型。在低收入阶段,农业政策主要聚焦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化肥使用等手段来增加产量,以满足国内需求。然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显著提升,利润率相对下降,而农业由于相对较高的收益率,吸引了大量资本流入,农产品供给逐渐过剩,市场价格下跌。日本的农业政策逐渐从追求产量的经济政策转向保障农民收入的社会政策,通过政策调整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政策转型为日本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奠定了政策基础。
• 农民收入相对下降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20世纪5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相对收入下降,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扩大。1955年,日本农户家庭收入占社会平均收入的比例为77%,1958年降至68%。农民收入的相对下降不仅影响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削弱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为了扭转这一趋势,日本政府开始关注农民收入问题,通过政策调整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提供了经济动力。
• 进口农产品对国内农业的冲击
20世纪50年代,日本相继加入国际货币组织及关贸总协定,逐步开放了农产品市场,大量进口农产品对国内农业造成了冲击。随着进口农产品品种和数量的增加,国内农产品市场面临激烈竞争,导致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收入减少。同时,国内农业生产也受到了抑制,部分耕地出现撂荒现象。为了应对进口农产品的冲击,日本政府加强了对国内农业的保护和扶持力度,以稳定国内农业生产。
• 农业人口快速向非农产业转移
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日本农业人口快速向非农产业转移。在1955年至1965年的十年间,日本总体就业人口从92.6万人快速增加到4763万人,其中二、三产业的增长占到了全部就业人口增长的75%,而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则从1498万人下降到1000.86万人。这种人口流动趋势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的短缺和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 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与乡村生态环境污染
日本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固定资产税和居民税等直接税。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和老龄化的加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受到严重影响,导致对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的投入不足。同时,乡村生态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生活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为了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和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日本政府加大了对乡村地区的财政扶持力度和生态环境治理投入,推动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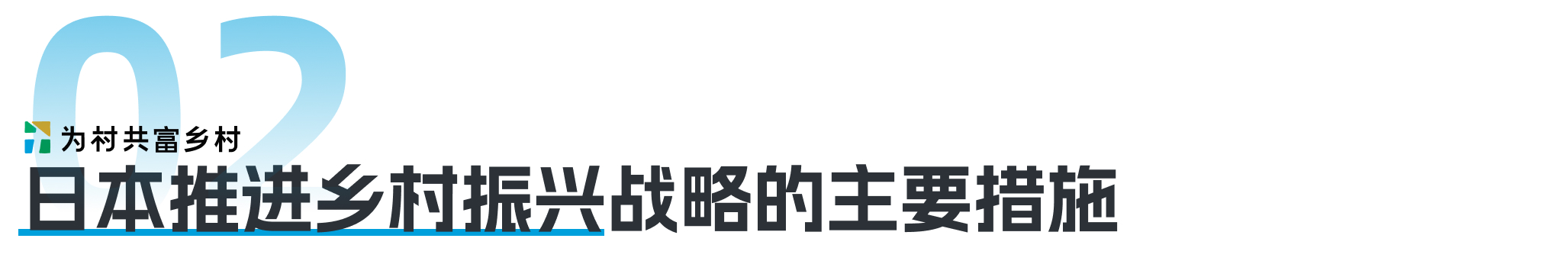
• 立法保障:构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
日本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高度重视立法保障工作,通过基本法和部门法相结合的方式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例如,《农业基本法》作为乡村振兴的纲领性法律,明确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目标;《山村振兴法》等法律法规则对需要扶持的乡村地区进行了具体界定和规划。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和规范,确保了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 完善体制:建立高效的乡村振兴实施机制
为了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日本建立了高效的实施机制。在中央层面,设立了专门的乡村振兴局负责综合性政策规划和项目实施;在地方层面,则建立了相应的农业科室等单位负责具体执行和协调工作。此外,日本还建立了乡村振兴联席会议机制等跨部门协调机制,确保中央和地方政策的衔接与配合。建立跨部委的轮岗制度,打破部门之间的业务壁垒,这些体制机制的建立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 财政扶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民福祉投入
在财政扶持方面,日本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福祉的投入力度。通过建设和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同时,通过直接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措施支持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日本还注重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和杠杆效应,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建设。这些财政扶持措施的实施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
• 村民自治: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
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日本高度重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通过推动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让农民直接参与到乡村振兴的各项决策和实施过程中来。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制度的实施,保障了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同时,通过组织农民参与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整治等活动,激发了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 以人为本,提升农业组织化程度与市场竞争力
日本为了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大力支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日本将合作经济组织称之为“协同组合”、“组合”和“金库”,这些合作经济组织是日本社会最为重要的市场经济主体之一。日本的协同组合种类繁多,业务范围覆盖了生产、供销、金融、保险、医疗等各个领域。通过政策扶持和引导,日本促进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规范化和规模化发展;同时,通过加强组织内部管理和服务创新等措施来提升组织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农产品销售、农业技术推广、延长产业链条、金融服务、合作保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提供了有力的组织支撑。
• 收入保障:建立多元化的农民增收渠道与保障机制
为了保障农民收入的稳步增长,日本建立了多元化的农民增收渠道与保障机制。一是增加经营性收入,发挥农业多功能性,促进环境保全型农业发展;二是增加工资性收入,促进农村工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和乡村旅游发展;三是增加转移性收入,在地理区位劣势地区发放直接补贴;四是增加保障性收入,增加农民养老收入,降低因病、因灾致贫的风险。这些收入保障措施的实施为农民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持,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提供了经济动力。

• 土地私有制制约农业现代化发展
自上世纪50年代起,日本伴随着快速的城镇化发展,农地被大量开发,用于工厂、住宅及公共设施建设,导致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然而,农地价格却随之暴涨,许多农民选择持有土地等待升值,而非进行耕种或出售。由于农业生产效益低,部分地区的农地长期撂荒。此外,大量土地产权关系复杂,甚至难以确认所有权,政府难以通过行政手段对农地进行有效集约。尽管采取了财政补贴和提高不动产税等措施,这一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农地撂荒与集约难的矛盾,使得具有生产意愿的经营主体难以集中土地,限制了农地规模化经营和大型农机具的使用,从而严重阻碍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步伐。
• 直接税制度引发地方保护主义
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利益矛盾。中央政府倾向于推动农业现代化,鼓励扩大经营规模,以提升农业的效率和竞争力;而地方政府更愿意引导劳动力回流农村,发展合作经济,保护小农户利益。这种分歧导致日本的农业政策呈现出摇摆特征:部分政策支持规模化经营,部分则偏向于维护小农经济。这种政策博弈虽然推动了政策的调整和发展,但从乡村振兴的实际效果来看,地方保护主义起到了关键作用。其根源在于直接税制度引发的财政利益冲突,导致地方政府更倾向于保护自身税收来源,而非完全配合中央政策目标。这种现象制约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同时加剧了政策执行中的矛盾与不一致性。
• 选举制度造成公共资源分配不均
日本的选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公共资源分配的不均。以基层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为例,村道建设完成后,其维护费用通常由村级财政承担。然而,一些经济薄弱的村庄由于财政能力有限,难以承担相应费用。这时,村长能否通过选举制度影响地方议员争取政府资金支持成为关键。若村长能够成功说服议员将本应由村级财政负担的费用转移至政府预算中,则该村的维护费用压力相对较小。反之,财政较弱但缺乏政治资源的村庄则可能面临更大的负担。这种现象反映了选举制度对资源分配的深刻影响,强村因政治资源丰富而获益,而弱村则因缺乏影响力而进一步陷入困境,从而加剧了区域间公共资源分配的不均。

• 统筹乡村振兴与现代农业发展
自《农业基本法》实施以来,日本围绕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因地制宜地采取了具有针对性的农业政策。例如,在北海道等地广人稀、具备发展农业规模化经营条件的地区,实施促进农业机械化、规模化经营的农业现代化政策。而在人口密度低、交通不便、难以集中农地的地区,主推乡村振兴政策,并根据城乡矛盾的变化进行政策调整。中国各地农业农村发展不均衡,财政预算资源有限,需要从各地的具体情况出发,以缩小城乡差距为目标,明确乡村振兴政策的适用区域,制定针对性较强的农民增收、改善乡村生活环境以及提升乡村福祉水平等乡村振兴政策。
• 夯实农民自治发展基础
农民是乡村振兴政策的直接利益关系人,乡村振兴政策是否切实可行,关系到乡村农民的切身利益。日本在乡村振兴政策制定、实施、监管各个环节始终坚持农民主体地位,让农民成为几乎所有乡村振兴项目的自觉参与者和真正受益人,既尊重了农民的首创精神,也激发了农民的主人翁精神,还提升了政策实施效率。对于中国来说,做好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必须始终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激发广大农民群众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监管制度,并且规范农民合作社的发展。
内容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