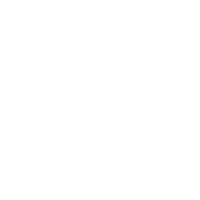12月16日,由腾讯SSV为村发展实验室、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北京为村互联网科技研究中心主办,腾讯学堂、腾讯北京总部党委协办的“为村讲坛”第四季第1期举行了。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作题为“乡村CEO社会价值创新评估——乡村转型中的企业家特征、行为与作用”的报告。
以下为内容摘编版:


• 乡村系统的特征
乡村是一个由地理空间、经济活动空间、熟人社会与非正式秩序共同构成,集农民、农地、农业和村落于一体的系统。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这一系统长期处于一种低水平均衡状态,其人、地、业、村之间具有自我调适与相互反馈的机制,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传统社会人不出村、耕作权为大的土地制度、小农经济以及熟人社会,从而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有机生态。在没有外力介入时,乡村系统能够维持自身的稳定与均衡。
乡村系统不仅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更是一个秩序的概念。其稳定性的核心在于它拥有一套内在的秩序结构:在传统乡村社会中,一是依托血缘与地缘的熟人社会,二是依靠宗族规范、村规民约、礼治与人情维持的传统秩序。这一传统秩序在集体化时期被国家权力改造,土地所有权几经变革,从而转向集体秩序。改革开放以后,乡村秩序再次发生深刻变化,集体功能逐步弱化,包产到户促使农户原子化,在治理层面则表现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共同发挥作用。
• 乡村系统的失衡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传统乡村系统的低水平均衡被逐渐打破,系统失衡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人
快速城市化推动了农民“离土出村”与农民分化。乡村常住人口从1978年的7.9亿减少至2023年的4.77亿,城镇化率由17.92%上升至66.16%。人口结构呈现老龄化,2020年全职务农劳动力平均年龄已超50岁;预计2035年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将达1.19亿,占比升至34.09%–35.24%。农户兼业化趋势显著,2003年至2020年,纯农户占比从11.18%降至5.07%,非农户从33.28%升至73.24%。同时,村庄人口外流严重,2016年近八成行政村为人口净流出,空心化率不低于5%的村庄占比57.50%,平均每村净流出409人,深度空心村占全部行政村的比例为29.98%。
地
尽管农民大量离土出村,传统人地关系并未根本改变。2020年人均耕地仅0.085公顷,不足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小规模经营格局持续,2020年经营10亩以下耕地的农户达2.32亿户,占比在85%以上。土地细碎化问题突出,2017年农户平均经营耕地约4.87块,超过六成农户拥有3块及以上,其中不足1亩的地块占比约65.25%。宅基地使用亦显无序,2020年拥有两处及以上宅基地的农户占比约8.71%,东部地区高达12.30%。土地再配置成本高、效率低,农地流转仍以农户间为主,2020年该比例为46.76%,规模经营推进缓慢。
业
农业就业结构失衡,2022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22.9%,却仅贡献7.3%的GDP,与发达国家农业就业占比通常为2%–3%相比,就业份额下降滞后于产值份额下降。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缓慢,2013—2020年种植业产值年均增长5.62%,其占农业总产值比重仅由52.5%微降至52.1%,主体地位稳固。与此同时,种粮成本持续攀升、收益下降,农业生产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且增长迟缓,制约了农业竞争力和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村
村庄数量持续衰减,自然村大量减少,行政村虽数量增加但普遍面临功能衰退与人口空心化,经济活力减弱。2019年全国村均集体资产为816万元,区域差距悬殊:东部地区占全国总量的64.7%,仅14%的村庄集中了全国约四分之三的集体资产。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置不经济,校舍、活动室等设施利用率低,公共厕所、健身器材等存在重复建设与闲置,适老适残化改造滞后。基层医疗和养老服务点普遍面临缺人、缺药与管理缺位问题。2024年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低于城镇19.7个百分点,城乡数字鸿沟明显。治理方面,传统血缘、地缘纽带弱化,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难以有效融合,治理效能低下,进一步加剧了要素外流与村庄的整体衰退。
• 乡村系统的演化
进入城乡融合阶段
中国的城市化已从快速推进阶段转向稳定发展期。根据诺瑟姆曲线,城市化率超过70%后进入成熟阶段(70%-80%)。2024年我国城市化率达67%,正处于这一阶段的起点,城市化速度明显放缓。在此背景下,需重点关注城乡融合时期乡村人口流动的新特征。
乡村人口流动特点
在城乡融合阶段,乡村人口流动呈现出新的复合特征。其一,乡村人口持续大规模外流。1978年至2020年,乡村人口由7.9亿减至5.1亿,占比从82.08%降至36.11%。城乡流动规模不断扩大,202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9753万人。其二,农二代发生代际革命。80、90后农二代已成为主体,2017年占比50.5%。相比农一代,其受教育程度更高、跨省流动意愿更强、从事农业比例更低。约60%缺乏基本务农技能,仅约10%在城市兼营农业,表现出明显的“入城不回村”倾向,与乡土联结日渐疏离。其三,流动半径呈现收缩与回流趋势。2023年外出农民工中省内流动占比达61.8%。区域上出现从东部向中西部回流,当年在东部就业的农民工减少1.1%,在中、西部分别增长3.1%和1.8%。同时,部分青年返乡下乡创业,2012至2022年底累计达1220万人。在此阶段,除关注农民进城外,还需重视“乡土粘度”,即农业在农民收入、生计与生活方式中的重要性,以及农民通过经济与非经济方式维持乡村社会网络的程度。
乡村经济形态变化
伴随人口流动与城乡关系调整,乡村农业经济形态呈现出渐进演化:
一是,农户家庭经营主体地位稳固
2022年我国从事农业经营的农户约2.33亿户,户均耕地6.69亩。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小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主体98%以上。
二是,农业经营主体结构发生变化
2021年土地流入各类主体的面积占比分别为:农户48.29%、家庭农场14.18%、专业合作社20.47%、企业10.05%、其他7.00%。
三是,农业产业形态趋向转型升级
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营业收入超18万亿元,现代农业产业园与特色产业集群加快建设。2023年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49万亿元,其中农产品网络零售额0.59万亿元;2024年休闲农业营业收入约9000亿元。传统文化活动也成为乡村经济新动能。
四是,村庄分化以及功能再造加速
村集体与农户收入差距显著,2022年最高与最低的10个村户均年收入之比达16.1倍。2019年全国村均集体资产816万元,但区域分布不均,东部地区占总量64.7%,仅14%的村庄占有全国约3/4的集体资产。村庄发展呈现三类格局:部分融入城市体系;部分依托地方资源与文化找到特色路径;大部分仍面临功能弱化、人口流失与社会活力不足的挑战。

• “发展型”村庄
该类村庄具有明确的发展导向、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与相对有效的治理结构。其运行机制以产业为支撑,推动人、地、业、村等要素联动,形成资源整合与功能转化的协同体系。关键秘诀在于村庄内拥有发展意愿强、组织协调能力突出的乡村企业家,能够构建与上级政府的良好关系网络,争取项目、资金等关键资源,并通过招商引资与企业合作,为产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 “治理型”村庄
此类村庄的主要功能是维持乡村社会的基本运行与稳定。其形成原因为人口持续外流,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村庄人口结构老化,土地、劳动力等资源闲置或利用低效,产业发展薄弱,经济活力不足。要素间失衡导致村庄缺乏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村组织能力主要体现在承担行政管理与日常维持工作,包括政策传达、矛盾调解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重点在于维持秩序与保障村民基本生活。
• 两类村庄对比
基于2019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对306个样本村的分类显示:发展型村庄仅占10.13%,治理型村庄占89.87%,后者在当前乡村中占主导地位。两类村庄对比如下:
人口流动
发展型村庄的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及劳动力总量均高于治理型村庄,年龄结构更年轻(60岁以上人口占比较低)。其以外来人口流入为主,外来人口与劳动力占比更高;治理型村庄则以人口流失为主,35.27%的村庄属于深度空心化。
土地利用
治理型村庄的撂荒耕地面积是发展型村庄的13.5倍,撂荒比重高出2.02%;空闲废弃宅基地宗数为发展型村庄的6.74倍,面积占比高出6.07%。发展型村庄耕地流转价格平均高出296.56元,土地流转市场更为活跃。
产业发展
发展型村庄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相对均衡,治理型村庄则以粮食种植为主导。发展型村庄从事本地二三产业的劳动力比例高出30.06%,治理型村庄从事一产的比例则高出20.09%。在新业态方面,发展型村庄有网店经营的村庄比重高出24.18%,经营网店的农户数量为治理型村庄的3.88倍;有乡村旅游的村庄占比高出27.94%,参与户数为治理型村庄的4.12倍。
村庄建设
在交通物流、信息通讯、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等方面,发展型村庄均明显优于治理型村庄。其人均可支配收入更高,村集体资产更雄厚,治理效能更突出;治理型村庄则普遍属于经济薄弱型村庄。

• 乡村企业家的定义与特征
乡村企业家是推动乡村发展的关键力量,其定义包含四个核心特征:第一,以村庄发展为本位;第二,具备发展能力(企业家才能);第三,能够盘活乡村资源;第四,带动发展、共享成果。
与传统乡村主体相比,其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目标上
不同于传统企业家追求自身或企业利润最大化,乡村企业家的行动围绕村庄与村民的整体发展利益展开。
二是,职能上
区别于传统村干部以维持村庄秩序为主,乡村企业家更侧重于推动村庄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三是,行动上
不同于传统小农自给自足、分散封闭的特征,乡村企业家能够整合村庄发展要素,带领村民共同参与,并积极对接外部市场与资源。
• 以腾讯乡村CEO作为研究样本
腾讯于2021年启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战略,将培育乡村职业经理人(乡村CEO)作为重点。作为市场主体,其发挥互联网企业优势,构建了“机制+人才+数字化”的乡村振兴支持体系,并与中国农业大学等单位合作,形成了一套涵盖遴选、培训、上岗的系统化培养流程。项目自2021年启动以来已实现规模化拓展,截至2025年上半年,培训覆盖全国17个省、68个市、311个县。
为系统评估腾讯乡村CEO项目的社会价值创新成效,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团队联合腾讯于2025年9月开展“乡村主体调查”。调查招募240名高校访员,采用电话访谈与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对乡村CEO所在村及对照村进行村庄与个体层面的调研。调查覆盖15个省(区、市)、58个市、128个县、近200个村庄,累计访谈337位乡村CEO及相关从业者、183位村干部。最终使用的有效样本包括243位乡村CEO,来自199个村庄,在地域、性别、年龄等方面具有代表性。样本量前五的省份依次为浙江、云南、广西、陕西、湖南。研究同时设置83个对照组样本,选取标准为与实验村庄地理邻近、资源禀赋相似且未参与腾讯乡村CEO项目的村庄村干部,以形成有效参照。
• 乡村CEO的特征
研究发现,经过腾讯乡村CEO项目培养的个体对乡村CEO工作的胜任程度明显更高,具体表现出以下明显特征:
人力资本普遍较高
乡村CEO普遍具有较高的教育资本,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复合型技能资本。
呈现年轻化特征
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新一代”乡村发展主体。
具有独特从业经历
多数乡村CEO在回村前曾前往距离家乡较远、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工作,并更多从事市场化主体的经营管理活动。
具备企业家才能
这既体现在其知识结构和能力储备上,也体现在其将理念转化为实践成果的能力上。
能够带领村民共同推动村庄发展
乡村CEO注重城乡资源对接,积极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农旅融合等产业,并着力挖掘乡村社会文化资源,推动农产品加工与品牌建设。部分乡村CEO还积极探索研学教育、特色种养、休闲养老等新业态。
• 乡村企业家的作用
总体来看,乡村CEO在推动乡村系统演化中发挥了多方面作用:一是打造并推广了更多具有辨识度的乡村品牌;二是更广泛地运用数字化工具开展村庄宣传与运营;三是积极申报并成功获批更多乡村发展项目;四是引入类型更为多样、规模更大的外部资源;五是通过加入乡村职业经理人相关组织,实现经验交流与抱团发展;六是逐步融入村庄治理体系,有的通过正式任职参与治理,有的专注于乡村发展与资源盘活工作,在此过程中深入挖掘乡村社会文化资源,回应村民诉求,并参与乡村规划与发展议程的制定。

评估结果显示,乡村CEO在推动村庄发展方面成效显著,具体表现在以下七个维度:
• 总体发展样态
乡村CEO所在村的“赋能乡村发展指数”快速提升,与对照村相比领先优势持续扩大,其在全部6个二级指标上均表现出更高的发展水平和增长幅度。
• 提升经营活力
乡村CEO所在村经营活力进步更快、优势明显,有效带动新业态快速发展,并显著促进人均收入提高;同时,乡村CEO有力推动村庄数字化水平提升,促进农产品等线上经营,并通过新业态发展为村民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
• 增强资源转化
乡村CEO所在村资源转化活力大幅增强,不仅提高了土地、资金等要素的利用效率,也显著提升了村庄的招商引资能力。
• 改善治理效能
乡村CEO助力乡村治理效能快速提升,推动治理数字化进程,促进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推广应用。
• 激活文化资源
乡村CEO积极挖掘与活化村庄文化资源,主要通过拓宽文化供给面等方式,增强乡村文化活力。
• 提升生态效益
乡村CEO带动村庄生态效益稳步改善,尤其在推动人居环境提升方面作用明显。
• 扩大政策影响
乡村CEO显著提升了所在村的政策影响力水平,通过加强媒体传播、争取政策关注、促进政企协同等方式,带动村庄在政策体系中获得更高能见度与支持力度。

研究采用双重差分法,从经济活力、村庄整体开发情况及主体发展情况三个方面,对乡村CEO的社会价值进行因果识别。评估以“村庄—年份”为基本分析单元,覆盖浙江、广西、云南三省2020-2024年间60000多个村庄的数据,通过整合夜间灯光亮度、土地利用及经营主体工商登记等多源信息,并统一至村级行政编码口径进行分析。同时,研究结合了三省乡村CEO的培训信息,将上述数据与各村庄进行匹配。
• 经济活力方面
村庄在引进乡村CEO后出现显著提升。分析显示,引进乡村CEO对经济活力的净效应约为0.65–0.74个亮度单位。若以引进前夜间灯光亮度均值24.7为基准,这一提升相当于经济活力增长了约2.6%–3.0%。同时,村庄内建设用地与住宅用地的地块数量明显增加,表明土地利用空间与效率得到提升,乡村CEO有效促进了村庄的整体开发,盘活了经营空间与闲置土地资源,且未对农地规模造成挤占,农地数量保持稳定。
• 主体发展方面
乡村CEO所在村的新注册主体以微型、小型为主,组织形式多为有限责任公司,行业分布集中于批发业、商务服务业与零售业。乡村CEO显著推动了村庄内经营主体数量的增长,尤其促进了小型经营主体的发展,并在文化艺术业、零售业及农业等相关行业的经营主体培育上作用明显。

• 结论
第一,乡村系统重构是实现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重要内涵;第二,乡村企业家是重构乡村系统的关键有生力量;第三,其实践显著助力乡村发展并取得积极成效;第四,有效嵌入乡村社会与治理结构是乡村企业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第五,要素重组与治理创新是推动乡村转型的核心机制;第六,人才培育与制度环境共同决定了乡村转型的可持续性。
• 政策建议
一是深化城乡要素配置体制改革;二是构建乡村企业家培育成长机制;三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四是构建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五是强化发展型政策导向与评估机制;六是强化制度供给与社会资本建设;七是循序渐进促进乡村企业家内生成长。
• 创新点
一是提出乡村CEO社会价值创新评估的理论框架,拓展了乡村发展与社会价值研究的分析视角;二是构建乡村CEO社会价值创新评估指标体系,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可操作的测量工具;三是将抽样调查与因果分析方法有机结合,提高了研究结论的解释力与稳健性;四是对乡村CEO社会价值典型案例进行了立体化剖析,增强了研究结论的现实指向性与实践意义。

内容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