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乡村职业经理人与共富乡村座谈会暨“为村讲坛”第二季第9期举行。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以“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共富乡村实践”为题作分享。
2023年,邱泽奇带领团队,先后到云南、重庆、广西、浙江等省市区的7个案例村庄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形成了《乡村职业经理人与共富乡村实践》一书。本期为村讲坛,邱泽奇重点分享了新书调研和写作背后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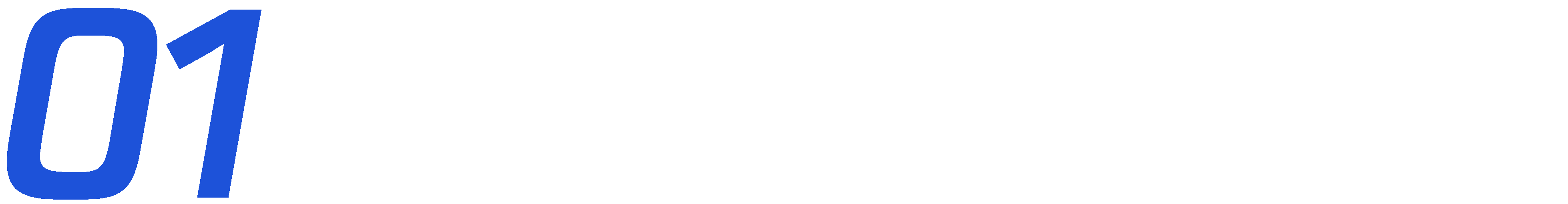
中国乡村发展的历史变迁
我在书的序言里写了一句话,“40多年,弹指一挥间,中国乡村却发生了‘千年之变’。在漫长历史的短暂瞬间里,从农民打工潮到乡村人才进城落户,从乡镇企业到现代工业,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中国乡村发生的是真正的历史巨变,让中国从农业社会快速趟过工业社会,迈进了数字社会。中国,因乡村的巨变而呈现历史巨变,因乡村发展的踏实脚步而迈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
要理解乡村职业经理人(简称:乡村CEO)与共富乡村实践,一定要将其放在中国历史、中国乡村的发展史中来看,而理解中国乡村的发展又一定要放在城乡关系的变化中来看。

新书《乡村职业经理人与共富乡村实践》宣传海报
过去的40多年是中国5000年乡村发展的最重要部分。其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乡村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是我们今天推进乡村振兴以及乡村CEO成长的背景。
先来看整个中国乡村发展史,大致可以分为四段:
20世纪前,中国基本处在传统农业社会。传统是指农业生产依靠人力和畜力,极少运用现代机械和其他技术。农业社会是指绝大多数人口以农业为生,农业生产形塑人们的社会交往与日常生活,形塑社会基本关系,包括城乡关系。
20世纪开始,工业化进程并没有立即改变传统农业社会的格局,直到20世纪后半叶,传统农业依然是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生计来源。
1980年,中国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还有80.61%,意味着乡村人口依然是中国人口的主体,乡村生活依然是中国人生活的基本形态,乡村产业依然是中国经济生活的基本格局,中华文明依然以农业文明为底色。
2010年以来进入城镇社会,中国城乡人口的比例持平,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0.05%;2023年底下降到33.84%。
在中国乡村发展史中,城乡关系的发展又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1949年前,是城乡关系的自然演化;1949年-1962年,城乡一体;1962年-1978年,城乡隔离;1978年-1997年,突破二元结构;1997年至今,不断重塑。
在1949年前特别是历史上的城乡关系自然演化中,城乡分野是人们的生计选择。初期的城乡关系表现为:在乡村,以村寨制组织农业人口的生产与生活;在城市,以市集制组织城镇人口的生产与生活,城乡分野是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共识。农业、农村、农民在制度上的主体性,让乡村社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是传统中国社会稳定且不断延续的基石。历史上,除了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复兴运动以外,中国的城乡之间没有隔离,人口的流动和职业选择是自由选择主导的自然关系。
而在1949年以后,国家主导工业化进程和人口流动,建构了新型的城乡关系。在1949年-1962年期间,在工业化优先战略推动下,城市人口急剧上升,而城市物质供应特别是日常生活用品包括粮食供应紧张,导致城市接近于崩溃状态。在1962年-1978年期间,城乡户籍制度阻止了人口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在1978年-1997年期间,1979年9月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980年9月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1983年末,中国99.5%的生产队都已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乡村劳动力的积极性,也让人口开始从乡村向城市流动,从农业向工业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流动。在1997年之后,城乡关系则进入重塑迭代的阶段,小城镇、建制镇、小城市、中等城市等逐渐放开落户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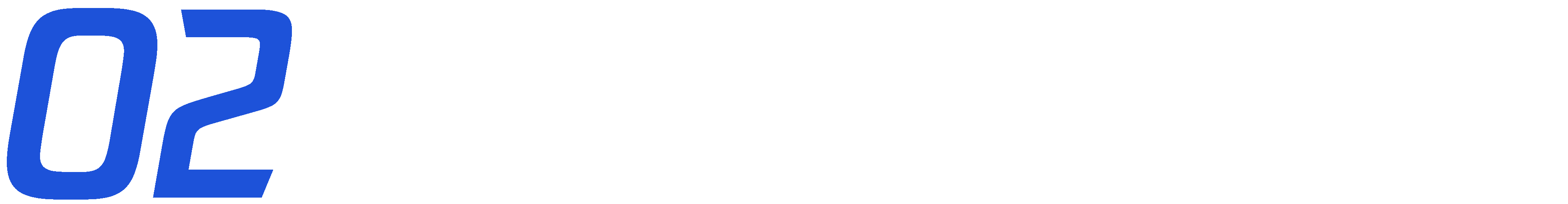
中国乡村巨变的三个阶段
从中国乡村发展史来看,中国发生的“千年之变”基本上发生在过去的40多年里。
这40年大致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后20年到21世纪初,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突破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从城乡人口比例来看,1980年,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61%,到2000年,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还有63.91%。这个阶段的核心变化是,突破城乡隔离,推动乡村工业化,推动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这个阶段的政策特点是,在国家政策引导下,突破城乡隔离,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了乡村经济发展的多元化,乡村人口进城务工。
20世纪80年代,乡村劳动人口开始在家门口兴办企业。1979年7月,国家发布《国务院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肯定社队企业在乡村经济中的地位。在社队企业之外,农村家户、联户兴办企业也悄然兴起,并逐渐发展壮大。1984年中央4号文件将社队企业正式改称为“乡镇企业”。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比如,以乡村集体企业为标志的“苏南模式”,以乡村个体私营企业为标志的“温州模式”,以港台产业扩散为标志的“珠江模式”等。
随之,乡镇企业发展带来的负效应也显现出来,如同业竞争、产品质量低下、环境污染、管理混乱等。1997年《乡镇企业法》实施,乡镇企业的发展被纳入法治轨道,作为中国工业的一个特殊类别也被正式纳入国家工业体系。
这个阶段另一个特点是农村人口外出务工。20世纪80年代,乡村劳动人口开始走出乡村,进入城市寻找生计。
随着1997年展开的乡镇企业改制,进城务工成为大多数乡村劳动力的选择。不过,进城人口在城际之间、不同区域之间的流动是不均衡的。按照通常的东、中、西部区域划分,我们发现,大多数中西部乡村人口的流动是跨区域的流动、跨省的流动,不是省内的流动;而东部地区的人口主要是在省内流动,跨区域的人口流动很少。
运用生计视角,这类现象是容易理解的。中西部乡村甚至城镇地区都没有足够维系生计的工作机会。因此,中西部的乡村人口不得不通过跨区域、跨省的流动来寻找生计。中西部地区不仅不能为本地乡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还因青壮年劳动力跨省外流而失去劳动力红利。2014年国家确认的832个贫困县基本分布在中西部地区。
第二个阶段大致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即消除乡村绝对贫困。从城乡人口比例来看,2010年,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0.05%,到2020年,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到37.11%。这个阶段的核心变化是,地区之间因资源禀赋和发展机遇的差异,导致乡村发展水平差异扩大,消除乡村绝对贫困,缩小差异成为国家推动均衡发展的战略选择。这个阶段的政策特点是,中国打响脱贫攻坚战,2013年开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战,2015年国家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2020年,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832个贫困县脱贫,2020年贫困地区乡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588元,年均增长11.6%。
第三个阶段从21世纪20年代起,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村振兴。2023年,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到33.84%。这个阶段的核心变化是,在乡村人口的基本生计获得保障的条件下,促进乡村整体发展,不仅有产业,还希望产业兴旺;不仅有绿水青山,还希望生态宜居;不仅人丁兴旺,还希望乡风文明;不仅组织完善,还希望治理有效;不仅“两不愁三保障”,还希望生活富裕。这个阶段的政策特点是,颁布了一系列乡村振兴相关文件,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国家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21年出台《乡村振兴促进法》……。
在这个阶段,人们都在寻找乡村振兴的解题思路。我们理解,推动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人才队伍是基石,乡风文明是灵魂,生态宜居是关键,基层组织是主导。相比2021年,2023年中国行政村的数量减少了近3万个,自然村减少了6万多个,偏远村庄和城郊村庄的消失已是不争的事实。
剩下的乡村又当如何振兴?
我提一个自己的观察:乡村是居住在乡村的人口的乡村,不只是乡村户籍人口的乡村。没有人,便没有乡村。对乡村振兴而言,人是最重要的。
以人为中心,这就提供了一种解题思路:让有能力的人来经营乡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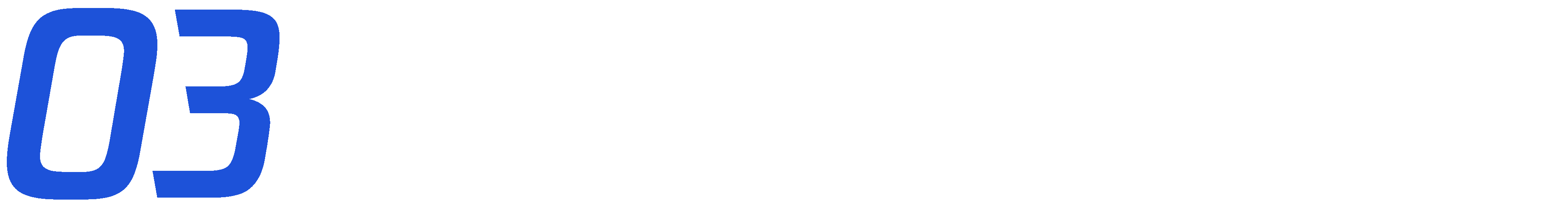
聚焦于乡村产业经营
浙江实施“千万工程”二十多年来,推动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有效缩小了城乡发展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乡村经营是乡村振兴和“千万工程”再出发的一项有效实践,也是实现共富乡村的有效路径。其中的关键是培养经营性人才,满足资源运营和业态经营的需要,为乡村发展注入内生动力。用人来吸引人是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
我们都知道产业兴旺重要,可是,没有人,产业兴旺就是一句空话。因为在既往的城乡关系中,人口外流,导致人才的匮乏;土地、房屋、劳动力等资源闲置,难以变现;以农业为主,产业单一,亟待丰富,增收效果有限,二、三产业发展面临人才、信息挑战。
在近些年的实践中,乡村产业振兴的路径也有不同的选择。早期的路径多为外部力量驱动的乡村产业发展,最典型的是早期的资本下乡,后来,资本下乡还有了各种各样的形态。资本下乡不是说经营不好,是农民站在自己的土地上,变成了土地经营者的雇工,成了客人。在这样的模式里,公司代替村庄,农民的主体性丧失了。
近期则开始探讨内外资源联结的内生发展路径。主要的特点是“农民主体+多主体参与”,动员农民真正参与进来,成为建设主体、运营主体和受益主体,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这其中,从经营人才为切入成为产业振兴的新突破点。
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经营乡村经营什么?谁来经营?怎么经营?
如果说传统乡村只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乡村,那么,在经历了脱贫攻坚战后,人们的生存已经获得了国家保障,乡村便不再只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乡村,而是需要发挥人们的能力而进一步发展的乡村。
在调研乡村CEO的共富乡村实践中,我们看到,一些闲置的房屋、土地等资源被盘活,农民把自己的资产变成集体公司经营的资本,通过入股成为经营主体,成为收益来源。这样一来,乡村CEO就变得特别重要了,把资源市场化、资产资本化,都需要乡村经营人才。
接下来的疑问是,经营人才为什么是乡村CEO,而不能是村两委。现在每个村庄大致都有两个组织,一个组织是治理组织,也就是村两委,另一个组织是村集体资产合作组织,即村级资产管理组织,是一个资产管理机构,不是一个资产经营机构。为了盘活资源资产,还需要一个商业运营的公司,没有这个公司,村集体经济是不可以盈利的。这个公司和村集体资产管理合作社紧密联系,受资产管理机构之托,就可以运营集体资产进行营利性商业活动了。乡村CEO就是受聘于这家公司的,是关键的乡村经营者,通过招商引资、自主经营、委托经营等多种方式,盘活和有效利用村庄经营性资产,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村庄产业振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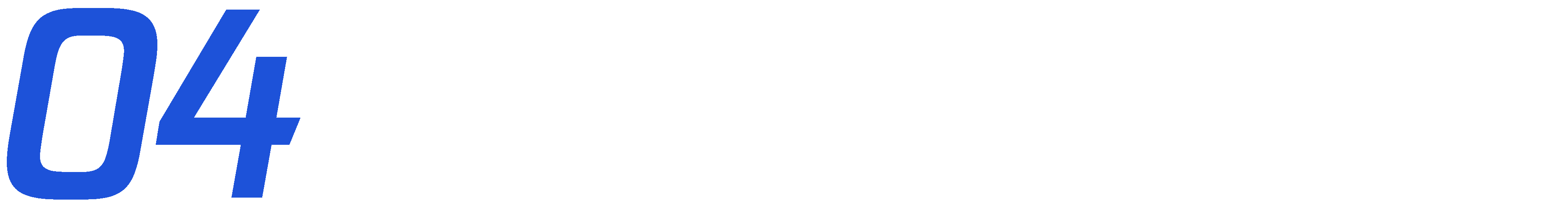
实践共性:多主体合力+数字化赋能
乡村CEO如何带领村庄实现共富?乡村实际经营状况如何?与其他主体的配合协同情况又如何?
在乡村CEO与共富乡村实践的调研中,我们选择了重庆、广西、浙江、云南等7处特点不一、产业发展路径与成效不同的乡村开展调研。
这些村庄均引入了乡村CEO进行乡村经营,乡村CEO协助盘活村庄资源,参与业态规划与运营,参与设计以农民作为收益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乡村CEO的经营实践,乡村资产得到有效运营。
共富乡村的实践是一个多阶段、多主体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我们进行了阶段性的归纳,发现这些村庄实践的共性为“多主体合力+数字化赋能”。
多主体合力是指“政府主导、农民主体、企业助力、社会共创”。
政府主导包括:总体规划,财政支持;组建专班,组织协调;运营指导,差异化运行。
农民主体包括:自身利益与乡村产业振兴链接;农民作为经营主体、决策主体、建设主体、受益主体。
企业助力包括:乡村人才培养,注入发展资金,提供数字工具、数字化运营支撑。
社会共创包括:参与乡村发展与业态规划,机制设计,助力人才培养等。
乡村CEO是“多主体合力”中内外部资源链接的关节点,兼具职业性和乡土性。
相较于政府,他们专门从事经营活动,聚焦在农村集体经济领域,经营专业性强。
相较于村民,他们有更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善于连接乡村和外部市场,善于整合资源、发展品牌。
相较于企业,他们有更丰富的“在地化”经验,是数字化经营工具的深度使用者,助力企业的数字化工具创新。
相较于社会力量,他们有更丰富的“在地化”经验,是经营设计的践行者,也为高校理论创新提供素材。
数字化赋能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数字工具主要的功能包括乡村业态推广、连接外部市场、落实利益分配、辅助村务治理。
数字化赋能人才对乡村资产的高效经营,数字化平台助力乡村资源整合变现,数字工具促进乡村多业态融合发展。
数字工具承担了农文旅产业的管理运营职能,使得利益分配机制高效透明运行,助力提升整体性服务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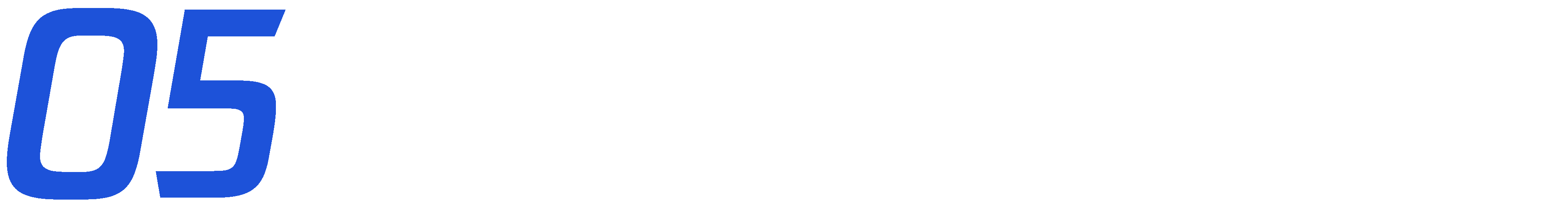
共富乡村与中国式现代化
在我看来,乡村的现代化主要的有三个方面:产业现代化、生活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
乡村CEO的共富乡村实践对这三个方向都有积极的影响。
● 在产业现代化方面,盘活僵化资产、产业提质增效。打破原先乡村以农业为主的单一产业结构,探索更加丰富多元的业态。充分发挥数字化工具在连接主体、对接市场、利用信息、提高效率等方面的优势,比如,云认养是新型数字工具,助力农产品销售渠道的拓宽。对于拥有独特自然风光与民族文化的村庄,开发多样化业态,走一三产融合的道路,利用公众号、视频号、云服务小程序等数字化工具,为建设乡村旅游品牌、加大品牌营销推广力度、拓展农文旅融合产业市场提供便利。
● 在生活现代化方面,优化生活硬件、更新生活观念。硬件支撑包括人居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软件支撑包括农民围绕生活形态、生活质量而形成的观念、态度与品味要求,比如,整洁的民宿彰显村民对于自己日常生活环境的期望与要求。
● 在人的现代化方面,培育农民主体意识、激活内生动力。村民需要具备市场意识,即将自己当作村庄的主人、资源的主人、产业的主人、生活的主人与环境的主人。村民需要具备市场意识,即面向市场组织生产、经营、销售,而不是以“等靠要”的姿态,通过“福利”或“帮扶”的形式获得所需资源。村民需要具备开放意识,即包容接纳的心态和能力。
总之,产业现代化为促进乡村繁荣、带动农民增收提供动力,生活现代化为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促进城乡融合铺平道路,人的现代化为赋能农民主体、促进乡村共富奠定基础。
乡村要实现的是产业现代化、生活现代化,最为重要的还是人的现代化,乡村CEO的共富乡村实践,首先是让乡村的资源、资产能够火起来,而比火起来、比赚钱更为重要的是,在赚钱的过程中让,农民的腰杆挺起来,能够更为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