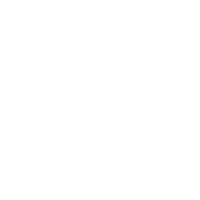9月10日,由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为村发展实验室、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北京为村互联网科技研究中心发起,腾讯学堂、腾讯文化、腾讯北京总部党委协办的“为村讲坛”第三季第11期举行。
中国农业大学县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张正河作题为“中国三农问题、走势及对策”的报告。
以下为内容摘编版:


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村考察时曾感慨道:“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
一份珍藏在博物馆里的“红手印”契约,记录了农民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探索中的勇气。会议结束后,生产队的土地、农具、耕牛等按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轰轰烈烈的“大包干”由此拉开序幕。而由这18枚红手印催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中国现代农业的一种生产经营方式,不仅极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也再次释放了生产力,并在1982年得到中央的全面推广,成为中国农村改革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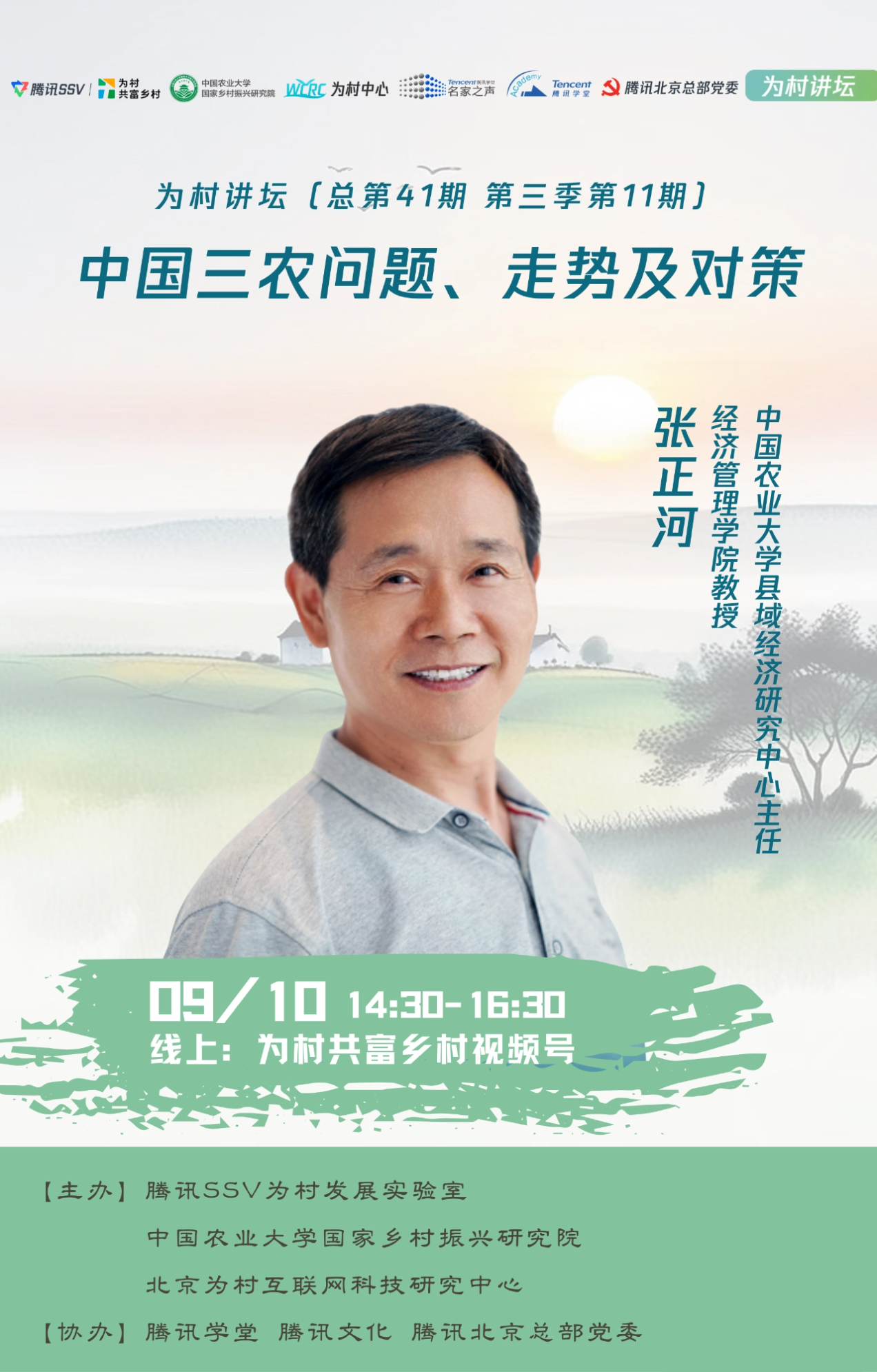
基于改革实践,中国“三农”发展可概括为“三步曲”:
• 1980年前后-1985年前后:粮食生产爆发期。1982-1984年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率达7.83%,从“吃不饱”转为“卖粮难”,农民“造田”积极性高涨。
• 1986年前后-1997年前后:乡镇企业崛起期。农民在粮食富足后转向非农产业,“五小工厂”(小服装、小鞋帽等)遍布全国,1995年,乡镇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53%,形成“农民造厂”热潮。
• 1993年前后-至今:农民进城期。随着市场经济推进,粮票等制度取消,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流动,年均净流出约1000万人,30年间累计约3.3亿人,推动城镇化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7%升至当前的68%,形成“农民造城”趋势。
在发展中,也出现了结构性的矛盾。
一方面是,收入分配差距显著。2024年中国人均GDP达1.3万美元,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收入分配失衡问题突出。1978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317,2000年突破0.4的国际警戒线,2008年达0.496,2024年仍维持在0.45。洛伦茨曲线显示,实际收入分布偏向“绝对不平均”线,反映城乡、区域间收入差距尚未根本改善。
另一方面是,粮食安全与成本压力。粮食作为战略资源的重要性显著,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指出“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当前中国面临农产品成本竞争力不足的问题:2016年数据显示,中国主要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稻谷、小麦、玉米、大豆等)的单位总成本均超过美国,其中大豆成本为美国的2.32倍,人工成本更是高达21.24倍。
同时,农业生产面临“土趋坏、水趋坏”的挑战——城市扩张占用优质农田,新开垦土地质量较低;水资源分布不均,极端天气频发。尽管“光趋强、温趋高、气趋好”对作物生长有一定利好,但总体仍对粮食自给构成压力。中国向世界承诺“粮食基本自给,仅进口5%”,如何在成本高企、资源约束下守住底线,成为关键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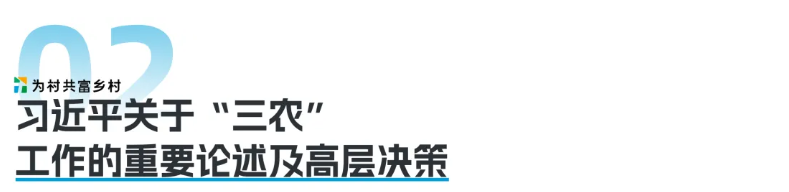
首先来看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脉络。
• 早期实践与理论奠基阶段:1969-1975年梁家河插队期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奠定对贫困问题的实践认知;1982-1985年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1990年在福建宁德提出“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倡导农业综合开发;1992年出版《摆脱贫困》,全面奠定了乡村振兴的理论框架和基础。
• 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阶段:1998-2002年任福建省级领导时,提出“南平经验”,完成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主张“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2002年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推进“千万工程”,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06年倡导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基本确立了“三位一体”的合作制理论。
• 全面形成与丰富完善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后,提出精准扶贫战略(2013年在十八洞村首次提出);2017年党的十九大部署乡村振兴,推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形成系统理论体系;牢固树立和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将“三农”强、美、富与国家强、美、富关联,实现高质量、高水平的发展目标。
在脱贫攻坚中,强调“精准扶贫”,提出“六个精准”“五个一批”,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问题。明确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要求“不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不丢下一个贫困群众”,2020年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
在推进乡村振兴中,提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将“三农”发展与国家现代化紧密关联。乡村振兴总要求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通俗概括为“钱儿多、地儿美、心儿顺”。明确农业要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要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农村要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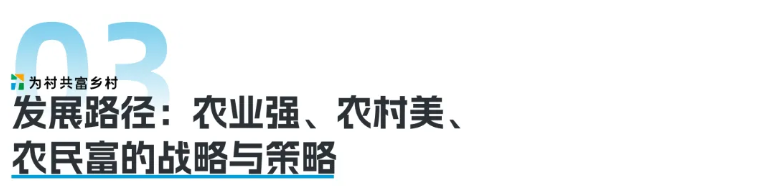
第一个大方面是:农业强,要构建现代化农业体系
农业强是农业强国建设的核心,需从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完善、支持保护强化、农业绿色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增强国际竞争力等六个维度协同推进:
提升高水平农业生产力。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为核心,通过现代物质技术装备提升农业综合产出能力。目前全国已建成11亿亩高标准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10.5亿亩,农作物机械化率提升至74%,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3%,农业生产稳定性显著增强,受灾面积较以往下降70%。未来需持续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确保农产品以合理价格满足市场需求,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健全全链条农业产业体系。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河南小麦产业为例,从传统种植向专用品种研发(如面包粉、饺子粉专用小麦)、面粉加工、方便食品生产等环节延伸,形成“生产+加工+流通+服务”的全链条模式,既提高附加值,又增强产业韧性。同时,强化产前、产中、产后分工协作,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产业从“单一生产”向“多元经营”转型。
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通过政策、资金、制度三重保障,确保农业经营主体“不亏本、有体面收入”。研究表明,农民收入达到当地城镇人均收入的47%~57%时,可视为“体面状态”,当前这一比例约为38%,需通过财政补贴、农业保险、基础设施投入等方式缩小差距。同时,避免补贴政策滋生“养懒汉”现象,聚焦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保障其合理收益。
推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破解农业面源污染(当前已成为三大污染源之首)和温室气体排放(约占全国总排放的20%)问题,科学利用水资源,合理控制农药化肥使用,探索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结合“双碳”目标,推动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协同,实现可持续发展。
培育高素质农业人才队伍。聚焦“人的现代化”,培养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包括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经理人、乡村治理骨干等。鼓励企业、高校参与人才培养,如培养乡村CEO等,助力提升农村经营管理水平,为农业强提供智力支撑。
增强国际竞争力与话语权。遵循“地道生产”原则,在优势区域发展特色、优质、标准化农产品。国家已划定大宗农产品(小麦、玉米、水稻等)和特色农产品(蔬菜、果品、中药材等10类)的适宜生产区域,按“在合适的地方种合适的作物”布局,可规避十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风险,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
第二个大方面是:农村美,要推动城乡协调与村庄优化
城乡关系规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不矛盾,而是相互促进,“没有富足的粮食,就不会有二、三产业的发展;没有现代化的工业与城市,就没有现代化的农业与农村”。发达国家城镇化率普遍超过70%,中国当前城镇化率68%,未来将进一步提升至75%~80%,农村人口持续减少是客观趋势。更多农民进入城市就业后,农村剩余人口可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形成“城镇化带动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支撑城镇化”的良性循环。
村庄演化路径。实施村庄分类差异化治理。根据村庄资源禀赋和发展潜力分类施策:一是一级、二级城市周边涉农区域,重点解决垃圾处理、村改居后遗症、失地农民保障等问题;二是乡集及中心村,优化宅基地管理,推进空心村土地整理,完善基础设施与生产生活分区;三是山区边际村和危险区域村庄,结合休闲旅游推进企业化运作,强化防灾规划;四是历史文化村镇,加大对古村落、传统民居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摸底与整理,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第三个大方面是:农民富,要实现收入提升与体面生活
明确收入目标与合理差距。农民“体面收入”的合理区间为当地城镇人均收入的47%~57%,对应城乡收入比1:1.75(当前约1:2.34)。这一差距既考虑教育年限差异(农村平均9年vs城市平均14年),也兼顾农村工作的自由度与城市工作的通勤成本等因素,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合理区间。
拓宽农民增收路径。一是产业带动,发展特色农业、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让农民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二是就业拓展,鼓励农民外出务工(当前农民工达3.3亿,带动5.5亿人在城市生活),增加工资性收入;三是规模经营,通过土地流转让少数“懂农业、爱农村”的主体耕种更多土地,降低单位成本,提升规模效益;四是政策补贴,通过粮食补贴、农业保险等保障基本收益;五是返乡创业,吸引乡贤、农民工返乡发展农业服务、农村电商等,创造就业岗位。
第四个大方面是:心里顺,要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推行“法治、自治、德治、贤治”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培育乡风文明,需重点激活四类权力主体的协同作用。
正式权力机构。以村党支部、村委会为核心,其治理效能直接关系乡村发展方向。选拔标准上,应优先选用“有经营头脑、一技之长、群众基础好”的能人型村干部,这类群体既懂市场运作,又熟悉村情民意,能有效带动资源整合与产业发展。同时需警惕两种倾向:“好人型”村干部虽人品可靠、人缘佳,但易因优柔寡断错失发展机遇;“强人型”村干部敢作敢为,但若缺乏监督约束,可能向“恶人型”转化,出现以权谋私、欺压百姓等问题。因此,需完善监督机制,同时鼓励返乡成功人士、大学生等群体进入村干部队伍,通过新鲜血液注入提升治理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
民间组织。针对经济组织、宗教组织等民间组织,要充分发挥其在资源对接、行为规范中的作用。例如,养殖协会能精准识别具备养殖能力和信誉的农户,在落实扶贫项目(如发放种羊、提供贷款)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行业协会可通过制定标准、组织培训规范生产行为,增强产业竞争力。
亲友合作圈。以家族圈和小家庭为核心,发挥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的治理效能。家族圈中,“长老”(辈分高、威望高、有能力的核心人物)具有天然号召力,通过做通“长老”工作,可带动家族数百人参与乡村建设,降低治理成本。随着社会变迁,“长老”可能不再局限于年长群体,年轻的带货主播等凭借影响力也可成为家族核心。小家庭中,需重视女性在家庭治理、邻里调和、乡村产业中具有独特优势——其亲和力与沟通能力能有效提升服务质量,应通过技能培训释放女性治理潜力。
精英与特殊群体。针对经济成功、品德良好的“强势精英”(如返乡企业家、退休干部)具有资金、资源、视野优势,可通过投资兴业、公益捐赠带动村庄发展,其示范效应能激发村民奋斗动力。对于村霸等黑恶势力,需依法严厉打击,铲除其生存土壤;对于神汉、巫婆等迷信群体,应通过科普宣传压缩其活动空间,避免其干扰产业发展,逐步以科学观念取代封建迷信,确保乡村治理的正向导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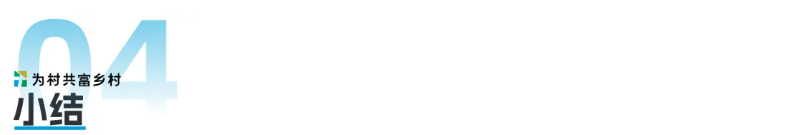
总结起来,未来的“三农”发展应持续遵循“顺天时、应地利、合人性”的原则。
在顺天时方面,应遵循经济规律(如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规律)、“五化同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等客观趋势,契合国家战略导向。
在应地利方面,立足本地资源禀赋(硬资源如土地、景观,软资源如文化、制度),避免盲目复制外部模式。例如,资源匮乏村可侧重发展劳务经济,而特色农业村可聚焦产业链延伸。
在合人性方面,尊重农民意愿,激发内生动力,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
最终以遵循制度规范和客观规律为基础,通过特色产品打造、创新营销等突破发展瓶颈。
内容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公众号